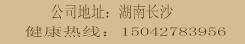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眼镜蚂蚁 > 眼镜蚂蚁的生活环境 > 高朋许春樵探讨小说ldquo怎么
当前位置: 眼镜蚂蚁 > 眼镜蚂蚁的生活环境 > 高朋许春樵探讨小说ldquo怎么

![]() 当前位置: 眼镜蚂蚁 > 眼镜蚂蚁的生活环境 > 高朋许春樵探讨小说ldquo怎么
当前位置: 眼镜蚂蚁 > 眼镜蚂蚁的生活环境 > 高朋许春樵探讨小说ldquo怎么
许春樵
探讨小说“怎么写”
比“写什么”更有意义
——周新民访谈许春樵
作者简介
许春樵,中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国家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放下武器》《男人立正》《酒楼》《屋顶上空的爱情》,中短篇小说集《谜语》《一网无鱼》《城里的月光》《生活不可告人》,散文集《重归书斋》等10余种多万字。中短篇小说曾获“安徽文学奖”、公安部金盾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当代》小说拉力赛冠军等。
访谈之后有彩蛋哦
注:周新民,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文学批评百余篇及专著多部,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各类项目十余种。许春樵短篇小说在风中漫游A风很大。不经意间,天就黑了,小宝觉得这扑面而来的黑暗是被风卷过来的,于是,他按了一下门窗中控,升起的茶色玻璃就将风和黑暗堵在了外面。
面包车里安静了下来。
小宝打开车载广播,广播里播报的通缉令只剩下最后两句:凶手强奸杀害女导游后抢走一部红色手机和一个装有一千八百元现金的深棕色女式坤包,有知情者速与市刑侦支队联系,联系电话……
小宝一伸手关了广播,自言自语着:“播来播去有什么用,还不早跑了!”
小宝打开车灯,灯光照亮了荒凉的乡村公路和公路两边的大叶杨,大叶杨的树叶在深秋的风中漫天飞舞,今年的寒流好像提前来了。
南原皮革厂的女式皮鞋据说出口后很受俄罗斯三陪小姐欢迎,然而被皮革厂污染的河里,鱼虾在三年前一口气全死绝了,地下水从去年夏天起总有一股烂牛皮没煮熟的味道,眼见着皮革厂就没水做饭和泡茶了。小宝隔一天拉一车桶装纯净水送过来,皮革厂厂长喝着安全的水,嘴上的一圈小胡子激动得乱颤,为此他还送过一双残次品的皮手套给小宝。
十九岁的乡下孩子小宝在城里的“碧溪纯净水公司”打工。
送水这段路程足足有三十多公里,小宝想顺路带个人进城,给搭车人省点路费,自己一路上也有个伴说说话,可一年多过去了,没一个人拦他的车。
去年夏天一个空气沉闷的黄昏,小宝看到一位长得很像娟子的姑娘沿着公路匆忙地走着,小宝停下车问姑娘要不要搭车,姑娘抄起路边的一块棱角分明的断砖,“你敢耍流氓?我男朋友是少林寺出来的,就在前面的抽水闸那儿站着呢!”后来,小宝把这事跟娟子说了,娟子央求小宝,“你不要乱带人,好不好?”
小宝想,人家搭不上公交车,顺路捎上一段,这又不是干坏事,怕什么呢?
今天天气太坏了,路上不会有人的,估计连一个蚂蚁都不会有。
小宝越想越远,越想越乱,这时,一只误入歧途的灰色野兔跳到了公路中央,小宝本能地踩了一个急刹车,车灯紧逼下的野兔竖着耳朵慌不择路中一头扎进了路边的水沟里,水沟里的蒿草已经枯了,一沟死水却源远流长,他有些担心野兔会不会被淹死,这么个鬼天气,跑出来干嘛呢。
开车胡思乱想容易出事故,于是小宝又打开了广播,他想剩下的路上全心全意地听听音乐,差不多八点半就能进城了。按键下的频道在跳过一系列卖药、寻人、招租、转让、征婚等糟糕的广告后,最终停留在音乐台的波段上。广播里正播放S.H.E的歌《我不想长大》
我不想,我不想,
不想长大,
长大后世界没有了鲜花;
我不想,我不想,
不想长大,
宁愿就这样又笨又傻……
小宝正在歌声中琢磨人为什么不想长大时,他看到路边一个男人面对着呼啸的灯光,拼命地挥舞着手中的一条毛巾。小宝停下车,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外面风太大了,快进来!”
男人裹着一身冷风和满腔烟味迅速坐在了副驾驶的位子上。关上车门,男人望着外面无边无际的黑暗,说了一句,“窗外没有霓虹灯,太好了!”
小宝没听懂男人的话,他怕怠慢了搭车的男人,于是不假思索地就接了话茬,“城里的霓虹灯一到天黑就乱蹦乱跳,晃得我眼睛发花,交通台每晚都报道东台区出车祸,你晓得吧?东城那块地方霓虹灯最多。”
男人用毛巾使劲掸着自己全身的风沙和灰土,“城里不好,人心比霓虹灯还乱!”
小宝在灰沙呛人的气息中,借着车内黯淡的微光,看到男人推一个平头,穿一件与这个节令并不相称的军用棉袄,脸上似乎有一种缺少睡眠的烦躁,小宝问:“大哥,你去哪儿?”
B长大后小宝才知道,爸爸是得阑尾炎死的,也是深秋的夜晚,爸爸从地里割稻子回到家,还没捧起饭碗,肚子疼得在地上直打滚,叔叔和妈妈用胶皮板车将爸爸拉到离家三里远的公路边,总共拦了十二辆汽车,没有一辆停下来,等到医院时,天亮了,爸爸也死了,医生穿着白大褂,脸上弥漫着白大褂一样的白色恐怖,“怎么能用板车呢,就是用拖拉机拉来,也不会出人命的呀!”
那一年,小宝九岁。
那一年,九岁小宝最大的理想是长大后开拖拉机。
爸爸死后,第二年春天妈妈跟一个走村串户贩鸭毛的江湖骗子走了,从此下落不明。小宝跟叔叔一起生活,读到初中毕业死活不愿再读高中,他要用读高中的钱去学开拖拉机,叔叔说,“要学就学开汽车!”
十八岁的小宝是揣着汽车驾照进城的。
在小宝懵懂的头脑中,进城开车与挣钱和发财没什么关系,他开车只是想在半路上捎上急需要搭车的人,他对娟子说只要开着车满世界地跑,总有一天会遇到搭车人,说不定能碰到妈妈在半路上向他招手,小宝记得小时候发烧的时候,只要妈妈的手摸着他的头,烧就退了;小宝淘气的时候,只要妈妈看他一眼,他就会迅速安静下来,妈妈的眼睛很好看,“你说我妈会变丑吗?”小宝从怀里掏出皱巴巴的妈妈照片问娟子。娟子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娟子把这事跟爸爸说了,在城里建筑工地上烧饭的娟子爸手里握着黏着饭粒的锅铲说,“你要是再往刘拐岗跑,我就打断你的腿!”刘拐岗是小宝租住的棚户区,墙上到处写着青面獠牙的“拆”!
娟子跟小宝是一个村子的,从小学到中学都坐同桌,娟子不喜欢读书,她说见到书上的字就像见到饭碗里的苍蝇,小宝说他也是,见了书上的字像是吃了饭里的砂子,硌牙。娟子初中没毕业就来城里的建筑工地帮她爸烧饭了,小宝见娟子不读了,就对娟子说,“混到中考一完,我就去城里开拖拉机!”那时候小宝只知道乡下没有霓虹灯,还不知道城里没有拖拉机。
娟子爸说小宝是个孤儿,从小没人管教,胆子太大,外面坏人那么多,他却整天开着公司的车一路上找搭便车的人,迟早一天会把自己的小命给搭出去的。娟子将爸爸的担心和恐惧用短信发给小宝,小宝回短信说:“一年多了,没一个人敢搭我的车,好像人家怕在我车上被搭丢了小命。”
现在,瘦弱的小宝斜了一眼副驾驶座位上的平头,平头身子结实得像榆树门板,块头比自己要大两三号,小宝想,尺寸明摆在这呢,他肯定不会担心自己安全的。小宝安慰平头说,“大哥,你不用急,我保证先把你送到市一院,然后再回公司。”
平头说他爸要死了,正在市一院抢救,他去送救命的钱。
平头裹紧棉袄,嘴里吐出的声音比窗外的风还冷,“没想到你居然停了车,多大了?”
“十九。”小宝觉得平头站在外面受了风寒,就打开了车内的暖风出口,发动机里的热气源源不断地吐了出来,“大哥,你是第一个搭我车的人。我免费给人搭便车,可没人相信,还骂我。我爸就是人家不让搭便车,才死了的。大哥,你爸什么病?”
“心肌梗塞。”
“外面风沙好大,要不要开快一些?”
“不用,医生说撑不了几天。”平头好像对他爸已经失去了信心,神情有些麻木。
小宝问平头,“抢救心肌梗塞要好多钱吧?”
平头点点头,“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小宝说,“九百,房租二百,中秋节那天给我叔买了一部手机,带照相的,一千八,一年多,才余下两千块钱。我是跟我叔长大的。”小宝平时一个人开车很寂寞,总算遇到个搭他车的人,一激动,说起话来就像油箱漏油,堵都堵不住。
平头也许正沉湎于父亲不可救药的绝望中,所以说话不多,他问小宝,“纯净水的钱由你收?”
小宝说,“是呀,起初王杠头怕我把钱弄丢了,不让我带回公司,可一年多了,每月结算一次,总共六万多块,我一分没少过。王杠头是厂长,为一毛钱能跟人抬杠两天,我也是听他们厂里人这么说的。他送我一双皮手套,是个次品。”
平头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着火,车内迅速弥漫起苦涩呛人的烟草味,“今天带钱回来了吗?”
小宝眉飞色舞地说,“带了,这个月四千九,”他拍了拍胸前鼓鼓囊囊的夹克衫,“都在这呢,王杠头非要说我多收了他十一桶水钱,核对了四遍,是他算错了,我没错。”
平头突然拍了一下小宝的松软的肩,语气坚决地说了一句:“停车!”
小宝踩住刹车,一脸茫然,“大哥,你要干什么?”
窗外的风越刮越猛,无边的黑暗铺天盖地,整个世界像是沉到了海底。车灯在黑暗中切割出两束光亮,而光亮的尽头是更加的黑暗。
C娟子跟小宝同年,也是十九岁。小宝住的刘拐岗棚户区离娟子烧饭的建筑工地不到三站路,没事的时候,娟子会偷偷地带一些铁锅里烤得焦黄的米饭锅巴给小宝吃,小宝在棚户区苍蝇乱飞的路边买上一大把烤羊肉串给娟子吃。娟子说工地上那位少一颗门牙的工头蒋大叔老是要带她去山里泡温泉,还说要送她一个MP3,“我不喜欢泡温泉,可我太想要一个MP3了,王力宏又出新歌了,不要太好听!我能不能跟他一起去呀?”
小宝说,“你问问他,我们俩一起跟他去山里行不行?”
娟子还没来得及问工头蒋大叔,娟子爸知道了这件事,他将手中的菜刀凶狠地剁到栗树案板上,眼珠子都快蹦了出来,他只说了两个字:“你敢!”
娟子就不敢了。她又去找小宝,说爸爸的脾气像灶膛里窜起的火焰,很凶,小宝站在自己那间墙上糊满了旧报纸的出租屋里说,“年底老板给我发红包,我给你买一个MP3!”
娟子说,“说话算数!”
小宝说,“当然算数!你们工地食堂大锅里的锅巴真好吃。”
娟子说,“明晚我再给你送。”这时娟子的手机响了,她努努嘴,示意小宝不要吱声,她接了电话,“爸。我,我在惠民超市呢,就在工地边上。什么,你也在超市?”
娟子合上电话,脸色都变了。
小宝问怎么了,娟子说,“我扯谎被我爸戳穿了,怎么办呢?”娟子吓得快要哭了。
小宝说,“走,我陪你去见你爸,跟我在一起有什么不放心的!”
娟子苦着脸说,“我爸就怕我跟你在一起,他说你胆子贼大,迟早一天要出事!”
D平头拉开车门,纵身跳下面包车,他说,“我想吐!”
小宝紧跟着平头跳下了车。
车外的风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路边是一大片干枯的玉米地,玉米收净后,老乡们还没来得及砍倒玉米杆。平头蹲在玉米地边拼命地呕吐着,声音像是一头被宰杀的肥猪在垂死挣扎中哀嚎。小宝捶着平头僵硬的后背,“慢慢吐,不要急!你受凉了,早遇到我坐上车,哪会翻胃呢。”
平头干呕了一气,什么也没呕出来,过了一会儿,平头突然站起身,一把死死地搂住小宝的脖子,小宝感到喘不过气来,他很困难地挣扎着说,“大哥,你抽筋了,转过身子,我背你!”
平头松开手,双臂搭在小宝瘦弱的肩上,小宝半拉半扛着平头上了车。小宝觉得平头比一麻袋玉米还要沉。
车上坐定后,关了车门,风声就消失了。小宝喘着粗气,抓起坐位上的毛巾递给平头,“大哥,你把头扎上,会好受些。小时候我发烧头疼得要炸,我爸就给我扎上一条干毛巾,立马就不疼了。”
平头没接毛巾,他神情沮丧地说,“我没发烧。”
“怎么要吐呢?”
“中午酒喝高了。”
小宝说,“心情不好,就想喝酒,是吧?”
面包车在夜色苍茫的黑暗中,像一枚呼啸的子弹,急速狂奔。小宝想着把平头快点送到他爸身边。
乡村公路有些颠簸,平头闭着眼睛不说话。小宝说,“是不是我开得太快了?我怕你送钱晚了,耽误救你爸。有爸爸多好呀!我爸都死了十年了,死的时候才三十五岁。”
平头简单地应了一句,“三十五,比我还小一岁。”
小宝说,“我和我叔、我妈在路边拦到夜里十二点,拦了十二辆车,要么不停,要么就说不去县城,耽误了,我爸肠穿孔,路上就死了。”
平头进一步裹紧身上的棉袄,自言自语地感慨着,“真惨!”
小宝看平头似乎有些难言之隐,就毫无必要地问了一句,“大哥,你说你在窑厂掼砖坯,乡下窑厂,挣的钱不会有多少,是不是抢救你爸的钱不够?”
平头侧过脸,眯着眼睛看着小宝,“你打算借钱给我?”
小宝说,“我身上的钱是公司的,不能借给你;你要是不够的话,我积攒的工资有两千块钱,我可以借给你。实在不够的话,我再问问娟子身上有没有钱。”
平头突然睁开眼,声音也活泛了起来,“你就那么相信我,不怕我以后不还?”
小宝说,“你把身份证地址、电话号码留给我,你又不会跑到外国去掼砖坯,对不对?”
平头说,“那我的身份证要是假的呢?”
小宝说,“不会的。用假身份证的人怎么会花钱给他爸治病呢?”
平头说,“用假身份证的人,根本就不会有一医院里。你听明白了没有?”
小宝有些疑惑,摇了摇头,“没听明白。”
平头说,“你没听说前几天市里发生过一桩抢劫、强奸的杀人案吗?”
E那天工地的黄昏异常宁静,脚手架和高楼的骨架浸泡在夕阳温暖的余晖中,纹丝不动。小宝给附近的一家专医院送完水,准备回公司,见工地上的民工正开晚饭,他停下车,在大铁锅米饭锅巴香味的指引下,找到了娟子,娟子跟他爸在给民工们打饭盛菜,他看到娟子的鼻尖上都冒汗了。娟子见到小宝,没说话,从锅底铲起足有两只鞋底大小的锅巴迅速塞给小宝,并用目光示意他快走,小宝没理会,接了锅巴后对娟子爸说,“根叔,要不要我帮忙呀?”
娟子爸头也不抬地剋了他一句,“你不要在这添乱好不好?”
小宝很夸张地将嘴里的锅巴咬得“嘎喳、嘎喳”地直响,他对蹲在地上埋头吃饭的一大堆民工说,“你们谁要逛四牌楼的,我顺便捎你们过去。顶多坐七个人,超员交警逮到要罚款。”
民工没人反应,小宝说,“我是免费的!”
那个尖嘴猴腮的民工显得比别人要聪明得多,他将最后一口饭扒进嘴里,站起身用筷子指着小宝说,“刚刚听的收音机,说这城里的免费体检、免费照相、免费抽奖、免费听讲座,都是假的。”
另一个戴着眼镜的民工看上去比较有文化,他凑过脑袋认真地推敲和分析着小宝的表情,然后语气平静地问,“你是不是姓雷?”
小宝说,“我不姓雷。”
眼镜民工说,“这就对了嘛,你又不是雷锋,还专门跑到工地上来做好事?带到城里后,你会说不收费,但各位给点油钱就行了。”
小宝说油钱也不要,民工们都笑了,小宝在民工们的嘲笑声中钻进了送货的面包车,他很生气,发动车子后,对着窗外一群民工莫名其妙地喊着,“我叔要给驾驶员油钱,可驾驶员就是不肯带,我爸半路上就死了。”
没有一个民工听懂小宝说的是什么,娟子问爸爸,“小宝说的是真的吗?”
娟子爸说,“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他爸医院,也是死。他爸死了,他妈跑了,这孩子没心没肺的,脑神经有问题,别跟他来往,听到没有?”
风好像停了,前方的灯火越来越亮。不久,车窗外就有霓虹灯活蹦乱跳了起来,车进城了。
面包车急速行驶中,平头的脸被窗外的霓虹灯切割成五彩斑斓的碎片,在一个亮着红灯的十字路口,小宝看到平头的正面很像他们公司里的那位物流部部长,严肃得有些严峻。
平头的目光严峻地盯着窗外,“我讨厌霓虹灯!”
小宝说,“霓虹灯太晃眼。”
面包车在市一院蹦跳着绿色霓虹灯的大门口刹住了,小宝一脸轻松地说,“到了。娟子老是怕我遇到坏人,我跟她说搭我车的坏人还没出生呢。”
平头终于从严峻的脸上挤出一丝轻松,他拉开车门下车,对小宝说了声,“兄弟,谢谢你了!以后开车不要什么人都带!”
小宝正要说“难道带你带错了”,话还没说出口,只见平头推上车门就走。谁知平头刚一转身,军用棉袄后面掉下一把二尺多长的杀猪刀,脑后居然有一绺足有五寸长的刀疤。
小宝吓得一脚蹬到了已刹死了的油门上,面包车像是被掐着脖子在原地一阵暴跳如雷,他一时脑子没拐过弯来,头上冒出了冷汗。
平头弯腰捡起杀猪刀,迅速塞进棉袄后面,他将头伸进车窗里,和颜悦色地对小宝说,“兄弟,吓着你了!杀猪刀防身用的,城里太乱,我们乡下人总是被城里人欺负。”
小宝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我还以为遇到坏人了呢。”
平头说,“还是当心点好,兄弟,谢谢你了,再见!”说着就医院玻璃大门内,进门后,一眨眼,人不见了。
小宝心情很好地给娟子回了一条短信:终于有人搭我的车了,安全送到了市一院。
发完短信,小宝松开刹车,一踩油门,面包车像一条快活的鱼钻进了城市的灯海里。
F小宝将车开回公司已是晚上九点二十分,物流部部长郭标听小宝沾沾自喜地说了自己的一通助人为乐的事迹后,鼻子都气歪了。“你他妈的胆大包天,竟敢用公司的车干私活!”
小宝本以为要被表扬一番的,没想到当头一盆冷水,泼得他手脚冰凉,他争辩说,“郭哥,郭部长,我跟你说过了,没收人家一分钱。人医院给他爸救命的。”
郭标是公司裘总的小舅子,号称公司二当家的,他拿出二当家的权威拍响了桌子,“你还嘴硬,没收钱?你以为你是雷锋了。我再问你,你要是捎了一个抢劫杀人犯,半路上把你卸成八块,怎么办?你死了也就罢了,公司的车十几万一台,被劫了,找谁赔去?”
饿极了的小宝狼吞虎咽地啃着饭盒里的冷馒头,一嘴的含糊,“那人家要是得了重病,医院抢救,也不带?”
郭标斩钉截铁,“不带!急救有。你回去写个检讨交给裘总,保证以后再不犯类似的错误,听到没有?”
馒头噎在小宝的喉咙里,他很困难的点点头,既像是表示同意,也像是表示听到了。
小宝一直没交检讨,也没人追着要,此后的日子里,小宝依旧隔天去郊外送水,却再也没遇到过半路搭车的。小宝对娟子说,他不会主动停车捎上路人,要是路人招手拦车,他还是要停的。“平头下车的时候,对我说了好几遍谢谢!”
娟子说,“平头身上揣着杀猪刀,半路上还叫你停车,这不太奇怪了,医院救他爸的吗?”
小宝说,“开始也有点想不通,后来我就明白了,他爸虽活不长,可也不是当天就要死,平头心里难受,加上中午喝了点酒,才要停车的。刀是防身的,我都跟你说过一千多遍了。”
娟子说,“工头蒋大叔说,我跟你在一起没有安全感。”
小宝说,“你怎么能跟工头说这事,你去山里泡温泉了?”
娟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MP3,喜形于色,“没去泡温泉,去百货大楼遛了一圈,这是蒋大叔送的,你看,棒极了,里面下载了三百多首歌,在一休网吧下的。要不要我借给你听几天?”
小宝有些无名的恼火,“我不听。你凭什么要蒋大叔的MP3?”
娟子反击,“你说年底用老板发的红包给我买一个MP3,那我又凭什么要你的?”
小宝一时回答不上来,他说,“你爸晓得蒋大叔送你东西吗?”
娟子说,“不晓得,他要是晓得了,还不把我脑袋拧下来当水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太凶了。”
小宝在工地见过工头蒋大叔,头顶上几缕稀薄的头发欲盖弥彰的掩饰着光秃秃的脑袋,被香烟熏黑的嘴里还少了一颗门牙,身上终年缠绕着死鱼的气息,他全部的底气来自于腋下的皮包里塞满了钱。小宝对娟子说,“我要告诉你爸。”
娟子害怕了,掏出口袋里的MP3,“我还给蒋大叔去,你千万不能跟我爸说。”
小宝拉起娟子的手,“走,现在就去还,我跟你一起去!”
娟子甩开小宝的手,“去就去,反正我已经听过好几天了,不听了。”
初冬的夜风冰凉,在一个霓虹灯缺胳膊少腿的茶楼里,娟子和小宝找到了正在打麻将的工头蒋大叔,工头蒋大叔说,“这是送给你的,好几百块呢。”
娟子说,“太贵了,借了听听就行了,”她把火柴盒大小的MP3塞到工头手里,“谢谢你了,蒋大叔!”
还没等工头反应过来,娟子拉着小宝的手一溜烟跑了。
来到灯火辉煌的大街上,娟子突然对小宝说,“医院看看平头的爸爸,好不好?”
小宝说,“走,现在就去,我早就想去了,可每天送货回来很晚。”
医院门口,娟子问小宝,“平头爸住哪号病房?平头叫什么名字?电话号码是多少?”
小宝愣住了。
G这年冬天的第一场雪铺天盖地,城市被连天大雪捂了个半死,小宝送水来回的乡村公路上每天都有车辆四脚朝天地翻在路边或趴在路边的水沟里,小宝却每次都安全归来。裘总说小宝车技真好,等公司做大做强了,就让小宝给他开专车,专车最起码是“劳斯莱斯”。小宝被空头支票煽动得热血沸腾,他对娟子说,“我本来的理想是开拖拉机,没想到裘总叫我给他开劳斯莱斯,据说是英国女王坐的。”
娟子问,“你检讨还没交呢,就让你开‘老子来死’,哪天去开?”
小宝说,“不是老子来死,是劳斯莱斯。”
冬天的晚上天很冷,他们在街边的一个烧烤店里边吃烤羊肉串,边说着闲话,这时吊在墙上的电视机里正在播放法制新闻,当镜头对准法庭上戴着手铐的抢劫犯时,小宝手里的羊肉串僵在半空中,眼睛都绿了,“太像了!”
“像谁?”娟子问。
小宝的目光继续咬住屏幕,“像平头,是他!不会错的。”
娟子说,“肯定错了,罪犯都长得差不多。”
第二天小宝在市里送水,他跟小虎私下里对调了一下,小虎替他送屠宰场,小宝改送是市中院,交换条件是小宝买一条半斤以上的烤红薯给小虎。小宝将一桶桶纯净水扛到中院的每个办公室,他在每个办公室里都问着同一个问题,“那个叫曹山镇的抢劫杀人犯,头后面是不是有一块刀疤,差不多有五寸长?”
每个办公室的法官们都觉得这个嘴上没毛的小送水工很好笑,他们都善意地说,“法庭不会根据他脑后面是不是有刀疤来定罪,我们真没注意到。你打听这干什么?”
小宝说,“不干什么。很像我那天晚上开车路上带的那个人,一模一样,也是平头。”
热心的法官喝着小宝送来的纯净水,又深入了解了具体细节,大家一研究,都说,“你看错了,完全不可能。你身上有四千多块钱,而且又是夜黑风高人迹稀少的乡村路上,如果是曹山镇的话,早把你杀了。这个凶残的杀人恶魔欠下三条人命,其中有一桩案子,为了抢二十多块钱,就把出租车司机给杀了。”
听法官这么一说,小宝也觉得有道理,所以他就强迫自己承认,肯定是看错了。
娟子见小宝好多天都絮絮叨叨地一会说看错了,一会又说肯定是平头,就劝小宝,“你以后不要再半路带人了,都快把你缠成神经病了。”
小宝后来又去市中院送过一次水,他问能不能让他见一下曹山镇,法官说这不行。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法官告诉小宝,元旦前要枪毙一批罪犯迎新年,曹山镇执行死刑的日子是十二月二十九号,“到时候你去北郊刑场,就能看清楚了,要是靠得近的话,甚至能看到他脑后面有没有刀疤。”
就在小宝准备再次跟同事调整送水班次去刑场的时候,裘总将小宝叫到办公室,平静而严肃地说,“你用公司的车子随意半路带人,对个人生命,对公司财物,极不负责;擅自调班,到法院打听案件,严重损害公司形象,公司早有明文规定,送水是服务性工作,不得对客户正常工作有丝毫的影响,更不允许形成干扰。”
小宝这才想起了自己确实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于是低着头诚恳地检讨说,“裘总,我错了,下次我一定改。”
裘总说,“没有下一次了。我已跟财务打过招呼了,多发你一个月工资。你还小,还不太懂事,将来找到新单位后,说话做事不要像大街上的霓虹灯一样,乌七八糟的乱蹦一气,一定要先用脑子想一想。”
送水的工作被老板判了死刑,小宝沮丧极了,小宝对娟子说,他要离开这座城市,去南方打工。娟子说,工地完工了,我爸见蒋大叔老来找我,他说城市里太乱要带我回老家种地去,小宝说,“你答应了?”
娟子说,“我没答应,也没不答应。我跟你一起去南方打工,好不好?”
小宝说好。
他们约好了十二月二十九号一起去刑场,不管曹山镇是不是平头,看完枪毙死刑犯,当天就走。
十二月二十九号那天清晨一起床,小宝就给娟子打电话,一直打不通,到了八点半,还没联系上,小宝以为娟子睡过头了,就一个人赶往刑场,等他坐摩的赶到北郊一片茫茫荒草甸子时,死刑已执行完毕,罪犯的尸体早就运走了。小宝抬起头,看到冻得硬邦邦的天空有几只乌鸦在盘旋,它们不遗余力地在寻觅着地面上的血腥。
小宝的心情很落寞,在回城的路上,他拼命地给娟子打电话,还是无法接通。
小宝直接去了娟子打工的工地,工地上空空荡荡,小宝摸到娟子和她爸住的活动板房,也是空的,一个看工地的老头缩着脖子,嘴里咬着半截香烟,见了小宝就说,“没有旧钢筋卖!”
小宝说我是来找娟子的,不是收破烂的,老头麻木不仁地说,“娟子昨晚跑了,她爸急得都要疯了,连夜出去找了,到现在也没回来。”
这天晚上,小宝在出租屋里收到了娟子发来的一条短信:我到海南了,蒋大叔给我安排好了工作,不要找我。
小宝急忙回拨过去,电话已关机。
小宝从没有温度的出租屋里走出来,屋里太冷,他突然想喝酒,于是他手里攥着上次娟子吃剩下的半包花生米,来到了棚户区小卖部的柜台前,小卖部老头认得小宝,热情地招呼说,“这大冷天,就着花生米喝酒最得劲,要二锅头,还是火烧刀子?”
小宝看着杂乱无章的货架,哆嗦着嘴唇说,“大爷,娟子会出事吗?”
“娟子是谁?”老头愣住了。
这天晚上,一轮圆满的月亮悬挂在深蓝色的夜空里,如同一面古代的镜子。
推荐阅读
陈峻峰
散文之见,或者常识
女人和男人不是梨子和杏子的区别
每天你都会有觉醒的一刻
温馨提示:《禾泉文学》的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如有侵权请您告知,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处理或撤销。
投稿邮箱
散文随笔诗歌图片类:
hqwk01
sina.转载请注明:http://www.yanjingmayi.com/myjt/92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