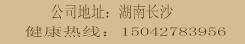儿童观
文/李小雨
如何看待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与儿童相处,折射出人们的儿童观。在历史奔涌的长河中,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不断变化,对待儿童的观念也是如此,有一个自足的发展过程。
古人时有“示儿”之作,比如苏轼《洗儿戏作》写:“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反躬自省,既表现出对孩子的殷殷期望,又蕴含着极为深沉的疼惜之情,这种富有多元层次的情感,非为人父母不可领会。辛弃疾在词里写“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清平乐·春居》)无忧无虑的孩童带给成人发自内心的愉悦之情,是自古以来所向往的一种天伦之乐。
当代文学作品中,也时常能发现儿童的身影,以下通过选读几位作家与孩童相关的描述,使我们体会儿童的特征与处境,从中也能触摸到他们所抱持的儿童观。或许,对眼下的社会境况也会有所启示。
”
《回忆鲁迅先生》/萧红
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啦!”我说:“来啦!”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鲁迅先生就问我:“有什么事吗?”我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崭然的会心的笑。海婴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头发或拉我的衣裳。为什么他不拉别人呢?据周先生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许先生问着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
“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
……(略)
看完了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先生又一定不肯坐,让周建人先生的全家坐着先走了。鲁迅先生旁边走着海婴,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去等电车去了。等了二三十分钟电车还没有来,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了,并且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地吸着烟。
海婴不安地来回地乱跑,鲁迅先生还招呼他和自己并排坐下。
……(略)
从福建菜馆叫的菜,有一碗鱼做的丸子。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许先生不信,别的人也都不信。因为那丸子有的新鲜,有的不新鲜,别人吃到嘴里的恰好都是没有改味的。许先生又给海婴一个,海婴一吃,又不是好的,他又嚷嚷着。别人都不注意,鲁迅先生把海婴碟里的拿来尝尝,果然不是新鲜的。鲁迅先生说:“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来,私下和许先生谈过,许先生说:“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哪怕一点点小事。”
……(略)
海婴每晚临睡时必向爸爸妈妈说“明朝会!”有一天他站在上三楼去的楼梯口上喊着:“爸爸,明朝会!”鲁迅先生那时正病的沉重,喉咙里边似乎有痰,那回答的声音很小,海婴没有听到,于是他又喊:“爸爸,明朝会!”他等一等,听不到回答的声音,他就大声地连串地喊起来:“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他的保姆在前边往楼上拖他,说是爸爸睡下了,不要喊了。可是他怎么能够听呢,仍旧喊。这时鲁迅先生说“明朝会”还没有说出来喉咙里边就象有东西在那里堵塞着,声音无论如何放不大。到后来,鲁迅先生挣扎着把头抬起来才很大声地说出:“明朝会,明朝会。”说完了就咳嗽起来。
许先生被惊动得从楼下跑来了,不住地训斥着海婴。海婴一边哭着一边上楼去了,嘴里唠叨着:“爸爸是个聋人哪!”
鲁迅先生没有听到海婴的话,还在那里咳嗽着。
”
按:萧红受到鲁迅先生举荐而进入文坛,与鲁迅一家关系较为亲密。在鲁迅逝世以后,她所作的这篇回忆文章,记载了大量的生活细节,这不仅是其文风的体现,也让我们得以从日常的角度来体察鲁迅。这些事实让我们知道,他不仅是一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猛士,一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知识分子,更是一位能够贴近孩童之心的智者,是当之无愧的爱心与责任心兼具的好父亲。
梅雨天放晴之后,萧红去找鲁迅,海婴看到她后直拉着她要一起玩儿,鲁迅对海婴的心理判断十分会心——因为萧红扎着辫子,于是海婴觉得她和其他大人不一样,是可以作为小孩的同类的。后来许广平问海婴,果然得到的就是这个回答。由此可见鲁迅对孩子心灵细微的察觉,他是能贴近孩子的心的。
最能体现鲁迅如何对待儿童的,也许是他“试吃丸子”这件事:恰好海婴吃的两个丸子都是不新鲜的,但别人吃的是新鲜的,便不注意海婴的感受,认为他是瞎胡闹,但只有鲁迅去试吃了海婴吃过的丸子,知道他吃的两个都是真的都不新鲜才嚷嚷的。鲁迅说:“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这说明什么呢?鲁迅对海婴有着天然的信任,并不认为他年纪小就无视他的感受。“一定也有他的道理”,就是充分尊重孩子感受和想法的体现。鲁迅不因自己是大人便傲慢地俯视孩子的体现,所以才会亲自加以查看,不无故抹杀孩子的说法。
在鲁迅先生生命将近的日子里,说话已经至为困难,但为了回应海婴“明朝会”的晚安辞,他用尽力气去喊出两声“明朝会,明朝会”,不能不让人动容,这是作为父亲的一颗滚热的心啊。
”
《从文自传》/沈从文
我有了外面的自由,对于家中的爱护反觉处处受了牵制,因此家中人疏忽了我的生活时,反而似乎使我方便了好些。领导我逃出学塾,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这人是我一个张姓表哥。他开始带我到他家中橘柚园中去玩,到城外山上去玩,到各种野孩子堆里去玩,到水边去玩。他教我说谎,用一种谎话对付家中,又用另一种谎话对付学塾,引诱我跟他各处跑去。即或不逃学,学塾为了担心学童下河洗澡,每到中午散学时,照例必在每人手心中用朱笔写个大字,我们尚依然能够一手高举,把身体泡到河水中玩个半天。这方法也亏那表哥想出的。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较大的关系。我最初与水接近,便是那荒唐表哥领带的。
现在说来,我在作孩子的时代,原来也不是个全不知自重的小孩子。我并不愚蠢。当时在一班表兄弟中和弟兄中,似乎只有我那个哥哥比我聪明,我却比其他一切孩子懂事。但自从那表哥教会我逃学后,我便成为毫不自重的人了。在各样教训各样的方法管束下,我不欢喜读书的性情,从塾师方面,从家庭方面,从亲戚方面,莫不对于我感觉得无多希望。我的长处到那时只是种种的说谎。我非从学塾逃到外面空气下不可,逃学过后又得逃避处罚。我最先所学,同时拿来致用的,也就是根据各种经验来制作各种谎话。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似乎就只这样一个原因,我在学塾中,逃学纪录点数,在当时便比任何一人都高。
……(略) 家中对这件事自然照例不大明白情形,以为只是教师方面太宽的过失,因此又为我换一个教师。我当然不能在这些变动上有什么异议。这事对我说来,我倒又得感谢我的家中。因为先前那个学校比较近些,虽常常绕道上学,终不是个办法,且因绕道过远,把时间耽误太久时,无可托词。现在的学校可真很远很远了,不必包绕偏街,我便应当经过许多有趣味的地方了。从我家中到那个新的学塾里去时,路上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有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又可看到一个伞铺,大门敞开,作伞时十几个学徒一起工作,尽人欣赏。又有皮靴店,大胖子皮匠,天热时总腆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上面有一撮毛!)用夹板上鞋。又有剃头铺,任何时节总有人手托一个小小木盘,呆呆的在那里尽剃头师傅刮脸。又可看到一家染坊,有强壮多力的苗人,踹在凹形石碾上面,站得高高的,手扶着墙上横木,偏左偏右的摇荡。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人,时时刻刻口上都轻声唱歌,一面引逗缚在身背后包单里的小苗人,一面用放光的红铜勺舀取豆浆。我还必需经过一个豆粉作坊,远远的就可听到骡子推磨隆隆的声音,屋顶棚架上晾满白粉条。我还得经过一些屠户肉案桌,可看到那些新鲜猪肉砍碎时尚在跳动不止。我还得经过一家扎冥器出租花轿的铺子,有白面无常鬼,蓝面阎罗王,鱼龙,轿子,金童玉女。每天且可以从他那里看出有多少人接亲,有多少冥器,那些定做的作品又成就了多少,换了些什么式样。并且还常常停顿下来,看他们贴金敷粉,涂色,一站许久。
我就欢喜看那些东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略)
”
按:沈从文的创作在当代文学中是非常独特的存在,他认为“美在生命”,并醉心于人性之美。这些认识的形成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很深的关联。读这一段沈从文自述童年生活的经历,于他的论点和性情能够有更深一步的体认。
在孩童眼中,生活中有趣味的事物实在太多了,磨针、造伞、制皮靴、剃头、染色、打豆腐、磨豆粉、屠户砍肉、扎冥器……,诸如此类的书本之外的生活,使沈从文常常驻足忘我。他似乎生有一双眼睛,能够发现这些事物中所包蕴的美和自然的道理。但这其实又是孩子们天然所有的对生活的观察和沉浸,是他们好奇求异的心灵需求,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本身便富于一种美,对这种美的注视和探索,能够给予人洞见与智慧,这应当就是沈从文在孩童时代便体认到的。
而在大人眼中,作为小孩子似乎就只应该懂事地去上学,静默地待着,不要给大人增添麻烦。好像上学、读书这些智识教育便可以完全地撑起一个人来,用大众化的标尺去衡量个性不同的孩子们,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说没有能力引导孩子对“美”和“思索”这类心理和精神的需要。但其实对美的体认,对思索的探寻,才构成了生命的底色,这些才是能持续为人提供营养的动力来源。
”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之后》/废名
此时莫须有先生同慈同纯在对岸道旁两株棕榈树下徘徊。这两株棕榈树真是长得茂盛,叶绿如翼,本是树上的叶子,人在其下但觉得美丽是叶上的天空。莫须有先生对之,自己的童心都萌发了,因为他小时最喜欢棕榈树。他观察两个小孩,慈是静,纯是动,静而笑,是如水中鱼乐;动而专一,是如蚂蚁工作。纯要爸爸替他摘一柄叶子下来,爸爸便点着脚替他摘一柄下来了。这一柄叶子,可谓“其大若垂天之云”,落在小小的手中了。纯奈何牠不得,于是席地而坐,说道:
“我来做一把扇子。”
他把他的叶子也放在地上了。他这时真感得这足下的地同地母亲一样,那么的可依靠,而他可他们的随便了,他想要依靠便依靠着了,而地母亲若无其事然。莫须有先生随手脱下了树上的叶子,因而有树上的残柄,好像受了创伤没有包裹似的,心里颇不自安,便叫慈回家去拿剪子来。慈拿来了剪子,莫须有先生将那残柄修整。莫须有先生这样做,一半是教训的意义,一半确是自己的美感,而慈也已经习惯于爸爸这样的教训了。莫须有先生学园工修剪时,这样同慈说话:
“我常常同少年人说,一个人作事,要有美趣,要求把事情做得好,最不可以因循苟且。”
莫须有先生说完了这句话,自己也得了一个教训似的,即是教训每每是无用了,远不如风景之足以感人。其时他的作工之手尚在叶绿丛,连忙收回来,即是说修剪工作完了,看了慈一面,看刚才的说话对于慈有无影响。慈望着棕榈树的叶子笑,爸爸的话明明没有影响了,人在自然之中一切都不过是“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即是说自然之中足以忘怀。剪子还在爸爸手中,纯仰首望着爸爸道:
“爸爸,你的剪子给我。”
于是小剪子便交付给纯了。莫须有先生这时乃觉得小孩真是可爱,即是说工作的意义伟大,而纯坐在那里渺小得有趣了。纯坐在地下,地母亲之大是不待说的,那棕榈树的叶子也确是大,而纯的小手同那小剪子一样是小。这剪子,纯知道,是爸爸自己用的剪子。这是一把钢剪,数年前莫须有先生在北平中原公司买的,“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纯慢慢地用牠将绿叶裁为团扇了。莫须有先生还是要同慈说话,他要说明因循苟且之害事,因为中国人最是因循苟且,他把剪子给了纯,然后又向慈说道:
“我在少年时也是因循苟且,便是懒惰,同时却是爱说大话,不求于事有益,是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后来在北平遇见一位老人,我从他得了许多好处,这位老人最大的好处便是作事不苟且,总有一个有益于事的心。我同他相处甚久,我看他每逢接着人家寄他的信,要拿着剪子把信封剪得一缝口,然后抽出信叶来,而我们则是拿着信撕破信封抽信看,这决不是小事,这样表现你不能把事做好,表现你迫不及待,要赶快看信里有什么奇迹似的,而且撕破信封对于寄信人也没有礼貌。我的这把剪子便是为了剪信买的,我学那老人的举动,练习把事做好,不匆忙。那老人家里,在茅房里,备有一个匣子,匣子里装满了手纸,我以为老年人是多此一举,现在才知道能够立事功的人都不是把自己放在意中,都是为别人作想,为小孩子作想,也便是民族主义。我的祖父是有事功的人。大多数的中国人能作什么事呢?因循苟且,当学生的还不知道爱惜学校的校具,几乎愈是少年愈是因循苟且,不讲公德,这样的人能爱国吗?所以少年人要有美趣,要求进步,从很小很小的事情上面练习工作的习惯。即如我刚才随手脱了这树上的一柄叶子,我觉得很对不起这树似的,为什么不拿剪子来好好地把牠剪下呢?所以我叫你回家去拿出剪子来把牠修整。”
”
按:废名师从周作人,被认为是“京派文学”的鼻祖。但若从儿童观上来看,废名与周作人也是甚为相契的。周作人提倡“儿童本位”论,而废名这一段写带着小孩用棕榈叶做扇子的文字,更是体现出他对儿童的理解和关爱,这种理解是从儿童自身出发的共情,是发自内心涌出的对儿童的爱。
小说主人公叫莫须有先生,他对着棕榈树萌发了童心,想起这是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树。这里不可轻轻略过,须知许多做了大人的人,已经全然忘记了自己小时候的感受和想法,这也是他们不能够体会儿童情感的重要原因,他们完全从自己出发,根本不会意识到儿童只是年纪小,但他们也有在发展中的情感和智识。
此外,莫须有先生“观察两个小孩,慈是静,纯是动,静而笑,是如水中鱼乐;动而专一,是如蚂蚁工作。”这又是他很了不起的地方,不仅能够用心观察儿童,更能够发现他们个性上的差异,并全然接受和欣赏,而不是横加指责,认为静便不如动,或者动又不如静。
接下来,莫须有先生围绕“美趣”和“不能因循苟且”两个方面,以孩子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去和他们谈话。他以自己经历过的人物和事情为例,这样便使事件真实可感,有天然的说服力,并且他举的例子是儿童可以听得懂,并且有所感知的,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便自然地对儿童完成一种美和意义的引导。能够对儿童讲这番话,首先体现出废名对孩子的无条件信任,相信他们在情感上能接受,在智识上能够有所体认,这是对待一个儿童应有的态度,对今天的社会和家庭仍有极大参考价值。
”
《儿童的文学》/周作人
我想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至于因了这供给的材料与方法而产生的效果,那是当然有的副产物,不必是供给时的唯一目的物。换一句话说,因为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我们供给他,便利用这机会去得一种效果,——于儿童将来生活上有益的一种思想或习性,当作副产物,并不因为要得这效果,便不管儿童的需要如何,供给一种食料,强迫他吞下去。所以小学校里的文学的教材与教授,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其次才是效果,如读书的趣味,智情与想像的修养等。
……
文学的起源,本由于原人的对于自然的畏惧与好奇,凭了想像,构成一种感情思想,借了言语行动表现出来,总称是歌舞,分起来是歌,赋与戏曲小说。儿童的精神生活本与原人相似,他的文学是儿歌童话,内容形式不但多与原人的文学相同,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或荒唐的思想。
……
小学校里的正当的文学教育,有这样三种作用:(1)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2)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3)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这(1)便是我们所说的供给儿童文学的本意,(2)与(3)是利用这机会去得一种效果。
……
幼儿前期
童话童话也最好利用原有的材料,但现在的尚未有人收集,古书里的须待修订,没有恰好的童话集可用。翻译别国的东西,也是一法,只须稍加审择便好。本来在童话里,保存着原始的野蛮的思想制度,比别处更多。虽然我们说过儿童是小野蛮,喜欢荒唐乖谬的故事,本是当然,但有几种也不能不注意,就是凡过于悲哀,苦痛,残酷的,不宜采用。神怪的事只要不过恐怖的限度,总还无妨;因为将来理智发达,儿童自然会不再相信这些,若是过于悲哀或痛苦,便永远在脑里留下一个印象,不会消灭,于后来思想上很有影响;至于残酷的害,更不用说了。
……
以前所说多偏重“儿童的”,但关于“文学的”这一层,也不可将他看轻;因为儿童所需要的是文学,并不是商人杜撰的各种文章,所以选用的时候还应当注意文学的价值。所谓文学的,却也并非要引了文学批评的条例,细细的推敲,只是说须有文学趣味罢了。文章单纯,明了,匀整;思想真实,普遍:这条件便已完备了。麦克林托克说,小学校里的文学有两种重要的作用,(1)表现具体的影象,(2)造成组织的全体。文学之所以能培养指导及唤起儿童的新的兴趣与趣味,大抵由于这个作用。所以这两条件,差不多就可以用作儿童文学的艺术上的标准了。
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又因为偏重文学,所以在文学中可供儿童之用的,实在绝无仅有;但是民间口头流传的也不少,古书中也有可用的材料,不过没有人采集或修订了,拿来应用,坊间有几种唱歌和童话,却多是不合条件,不适于用。我希望有热心的人,结合一个小团体,起手研究,逐渐收集各地歌谣故事,修订古书里的材料,翻译外国的著作,编成几部书,供家庭学校的用,一面又编成儿童用的小册,用了优美的装帧,刊印出去,于儿童教育当有许多的功效。
”
按:周作人持有“儿童本位论”,这在他的许多文字中都可以见出,他指出中国向来没有对儿童的正当理解,表现在文学中,便是忽略了“儿童的”这个特点,甚至也缺乏“文学的”特点。他明显是不满足于儿童能吃饱穿暖的,认为社会、家庭应当同时为儿童提供“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并能够“恰如其分地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他认为儿童生活对文学是有需求的,这无疑肯定了儿童的精神需要。而与此同时,又强调不要过分
转载请注明:http://www.yanjingmayi.com/mydc/8979.html